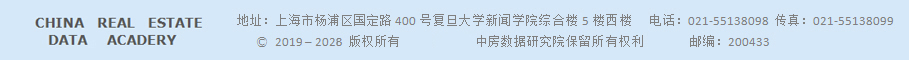| 刘煜辉:五问宏观面 |
|
| 发布时间:2013-10-23 10:47:22 来源:商业周刊 |
一、关于经济下行
有一种观点,长期和短期分开看经济。个人觉得不妥。原因是当前长期因素可能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非线性的时间窗口。长的短的分不开。
下行的强动力来自供应面(长期因素)。
中国的潜在增长可能处于加快下行状态。我一直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关注潜在增长变化可能是非线性的,某些时间窗口可能是突变的。这是源于生产率变化,严格地讲是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因素。虽然没有时间去搜索是否已有文献涉及这方面,但根据我的宏观研究的经验感知,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凯恩斯的“陷阱”其实描述的是投资回报率出现崩溃的场景。
白重恩(2013)的研究计算了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
这是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牵引力。
任何抗拒潜在增长下行的需求政策,最终转化的都是通胀的因素。目前cpi僵持的压力,正是政府不断阻碍经济出清的结果,大量要素资源(人工、资金、原料等)被无谓地消耗在低效的部门。你也可以定义它是一种滞胀,但这可能是一种非稳态(过渡),因为缩的压力一直在聚集(生产流通领域的通缩已经持续了17个月,且无收敛的迹象)。
从需求层面观察经济下行的动力,主要是大家已逐步形成共识的:债务率可能已经见顶。债务抑制了需求。债务周期的顶部区间,库存周期的下行期被拉长(我体会是“合意”库存水平的下移),去库的过程变得缠绵无期。补库的需求往往被喷涌而出的过剩产能所淹没,使得补库的过程很难持续且绵软无力(原料库存时常出现一些弱反弹,但产成品库存往往麻木而无法感知)。
融资成本高企,产成品的提价又受制于庞大产能释放,增加存货投资是不经济的。
债务堆积、产能过剩其实是从不同层面(实物经济和金融经济)讲同一个事情:生产率衰退(资本回报率的下行),需求面和供应面是高度统一的。
短线看9月旺季后,最近的原料补库将经受考验(8月上中旬发电量同比16.1%,上游补库是用电反弹的原因),如果厂商发现旺季提不了价,会重新回到去库的轨道,届时情绪的反扑可能会更加强烈。
二、流动性紧张的压力是内生的
无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悲观还是乐观,但大家对债务率已经很高了是共识。
债务高未必会崩溃。临界点是大家争执的焦点。风险的爆发(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呈现出很强的非线性。临界点的判断远比债务率的度量难得多。
债务临界点可能最敏感反应是流动性。泡沫破裂过程一定对应的是利率飙升。
发生在6-7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冲击,我的直感听到了“竹子断裂的第一声脆响”。至少我能体会到以下三点。
1、外汇占款供给基础货币的体系系统性崩溃。国际收支拐点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相对生产率的衰退,2009年以来经常帐盈余/GDP比例大幅下降,去年资产项目出现1100亿美元的巨额逆差(结束了近20年的双顺差格局),今年1季度虽然国际收支盈余录得一定的恢复,但结构严重变差,来源已不再是经济盈余,而是金融项目的对外负债的增加(大量的资金通过虚假贸易跨境套息)。这凸显出上半年宽裕的流动性状态脆弱性的一面。所谓脆弱性,是指流动性状态由之前的“易松难紧”转向“易紧难松”,这种变化确立是在2011年4季度。今年5月以后,一旦金融项目的套息活动得以遏制,外汇占款又重归去年的萎靡,流动性就会回到需要央行主动“关照”的状态。
2、不仅是金融部门,而是整体经济的流动性错配可能累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从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看,负债端久期明显变短,这是因为近年来以“票据+非银”的银行影子业务规模迅速地膨胀(票据融资最长不超过半年,而信托和券商资管产品的融资多为一年,少数2-3年的产品其存续期间也安排有开放赎回条款);但资产端却明显变长,大部分资金流向基建、地产和其他高杠杆低效部门,形成资金的沉淀,周转率大幅下降;从银行的表看,由于外汇占款的萎缩和产业部门回报率的下降,银行体系低成本负债资源趋于枯竭,近年来只能用更短的/不稳定的/高成本的负债(同业+理财)去支持其信用资产,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脆弱性。
3、庞氏状态的出现。由于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和低效率的部门,这些长期资产的现金流已不能够覆盖短期负债的成本。如此,举新债还本息模式开始繁荣。市场充斥着借短钱的融资客,这时候要求央行必须保证货币市场流动性充沛,一旦央行不及时对冲,短端利息就会快速飙升,这就是6月份的场景。而长短端利息倒挂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短端被“冰冻”必然传递至长端,高利息会导致经济加速下行,资产价格出现崩溃。
我以为,1、2只是准备条件,而3是关键性条件。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来自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债务失控。整个信用系统都在套体制的“利”。而由此形成的大量僵尸型企业和资产难以灭亡,并占据和无谓消耗着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导致经济生产率显著衰退。由于新增信用在越来越高的比 例上被用于支持既有债务体系的循环,所以货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差,流动性内生紧张的压力越来越大。
总之,当前的流动性压力是内生性的,因为债务见顶、经常帐盈余收窄、国际收支的拐点、生产率衰退都是一条逻辑线索。由此衍生的推论是,美国未来QE退不退出都不是决定性的,只是某种触发条件而已。
三、关于流动性的判断
应以“宽货币、紧信用”应对金融的脆弱性
政策选择的无序可能会加快临界点的到来。快速释放资金上涨内在压力,会导致债务负担迅速自我膨胀,若信用系统因此而陷入无序的相互践踏,资金链断裂和经济的硬着陆将会发生。央行试图节制经济错配的风险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宏观政策和审慎监管之间的分寸拿捏值得商榷。从宏观政策角度看,高债务率已经形成的场景下, 央行的取向应该是想办法如何有效降低既有债务系统滚动的成本,为下一步去杠杆准备条件,而不是相反。遏制债务主动扩张可能更多得倚重有效的审慎监管。
由于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是“万能”的。只要它愿意对冲,货币市场完全能保持5月份之前的流动性充沛状态。
央行6月7月的政策状态被研究者定义为中性偏紧的取向,央行似乎乐见被动收紧,表现为不主动通过逆回购去降低二级市场紧张因素,或者续做到期央票向市场传递乐见长端利率上升的信号,我以为,央行试图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抬高长短端利率,挤压信用端的策略,未必能达成理想的效果。理由有三。
一是在中国,借贷成本的上升往往产生的是“泥沙俱下”的效果,那些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未必感受到最大的紧缩压力,而全社会债务负担被动抬升,挤出负效应明显;
二是失控状态下,信用端利率快速上升会挤破泡沫,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我们不知道决策者是否做好了经济提前着陆的准备;
三是资金成本的上升可能很难压迫银行减杠杆,反而有可能激励银行出现利率市场化下的逆向选择,一是将更多资金投向平台和地产(7月份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增量合计仍保持在3000亿元的高位),或是减少债券的配置而为了保护流动性差、资产质量可能更差的非标债权,从而道德风险进一步凝聚。
在中国现行体制没有本质变化的情况下,我以为比较有效的方式:还是借助行政手段来定向抑制信用端体制内主体的行为(影子银行、平台和地产),如此,在货币端,央行就没有必要将银行间市场保持在一种紧张的状态,相反,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下有利于推进债券市场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从而修正全社会流动性错配的风险。这也正是央行周行长一直希望看到的目标方向。这是堵疏相容的政策组合(堵更多依赖审慎监管,而宏观政策要为疏创造条件,而不是相反,用宏观政策来堵审慎监管的漏洞)。
如此,我们将看到一种良性状态的出现:M1、M2和社会净融资增速呈现有序收敛态势,而货币市场利率也是下行的。货币政策这种状态在1998-2002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期也曾经出现过,即“宽货币、紧信用”,我称之为“衰退式宽松”。
我们看到政策建议正在被宏观层所认识,7月底央行开始重启逆回购,主动推低货币端利率水平。未来要实现全社会整体利率水平下行,从而降低整个债务体系滚动的成本(去杠杆的货币环境),不仅需要有效抑制高杠杆部门的增量需求,可能更有赖于要主动清理和终止一部分僵尸状态的存量信用,让它们不再无谓消耗增量信用资源。
有人问中国经济着陆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很简单,允许三个事情:1、允许僵尸企业关厂和破产退出;2、允许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在建项目下马停建;3、允许僵尸信用终止,即信用市场违约和银行坏债的显性化。现在的状态是大量的增量资源被消耗在这三个方向。无效经济部分挤出是目前融资成本高企的关键因素(生产率的衰退和经常帐盈余的萎缩)。
债市的长短期压力
最近债券市场调整的压力,主要源自流动性溢价的上升,风险偏好并出现被严重挫伤的迹象(期间利率债出现了明显调整,而与此同时小股票甚至创了新高)。银行开始调整其资产负债的结构,非标萎缩的压力释放,原来非标(目前主要是票据)对应的资产部分需要长期资金与之对应;全市场长期资金的需求因此上升。银行债券配置盘的需求受到明显挤压,一级市场招标结果经常很糟糕,银行参与程度差,呈现出一级市场收益率带动二级市场收益率上行。
债市调整的压力可能要一直持续到这种需求的下降,未来下降有两种情况:一是负债端非标融资模式重新反弹;二是资产端存量重组大力度的展开,终止部分僵尸信用。总之,一句话,要么重拾短端融资,要么长端需求衰退下来。
8月至9月份的阶段性货币边际改善可能会改善名义利率快速上行的压力,我们判断这主要是一在发生:即央行松动短端,错配模式重新恢复,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阶段性结束。但这个压力并没有解除并还在累积长大。靠中央银行一家之力是勉为其难的。它只是裱糊匠,哪漏风贴块纸。6、7月曾想试着揭盖子,最后发现糊涂了,办不了,所以又盖上了。
短线看是流动性溢价,中线看,债市最大的压力依然来自于风险偏好的下降,未来去杠杆过程中若政策失踞,出现无序相互践踏,信用风险溢价会出现飙升。
融资成本上升的关键因素是挤出
如何认识最近不少研究者认为的长端利率中枢的上升?
最近都是做债的朋友在讨论这个事,个人感觉其中有混淆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成分。讨论实际利率是一个宏观问题,而债券的估值只讨论名义利率。目前大家讲到的利率中枢上升压力,来自储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我体会这其实是讲一个经济体的影子利率的水平。
高储蓄高投资是一般性的常态。更有意义的是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即经常项目盈余。如果国内部门竞争力强,能从国外部门赚取盈利,收入增长强劲,表现为国内储蓄 增长会显著高于投资。这时资金价格是便宜,这是指实际利率。
从经济的影子利率看,中国的确存在刚性向上的中线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要持续到生产率重新回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会导致中国储蓄率进入明显下行期,我觉得决定性的是生产率衰退所导致的经常帐盈余的萎缩。中线看,经济发生缩的概率远大于胀,缩状态下,实际利率是上升的,但名义利率是下行的。
讨论名义利率,我不认为存在利率中枢的上行。
目前融资成本上升的关键因素是挤出。
一定需要关注中国经济体制内外的结构性差异,不同微观主体承受利率水平差异很大,对体制内主体而言,由于大部分信用资源向其倾斜,长端利率一直不高,特别是考虑通胀之后实际利率更是如此,多数情况下还是负利率。但是对于体制外主体,由于挤出,他们所承受的利率一直非常高。紧缩期情况更甚。中国金融制度的安排就是保体制内的。
单纯谈一个整体性的借贷利息的上升,模糊了严重的结构性差异。
反转过来讲,如果改革的话,无效率的部分受到挤出,货币的周转率提高的话,有利于推动名义利率整体下行。
四、关于中国的房地产
最近地产融资有放开的迹象,市场反应还是比较理性的。因为中国地产并不独立,它不过是地方投资的杠杆,融资的制度安排(通过地产商将家庭的储蓄转化为政府的收入)。你若真从财政和金融口抑制住了地方的冲动,地产根本不用管,起不了什么蛾子。我想上面领导可能已经想明白了。
最近大家讲得比较多的长效机制,我体会关键在于估值的修复。
中国地产估值存在的问题可以简化为:分子是权力配置资源的问题,分母是土地要素升值收益的分配问题。
分子看,近几年为权力定价的倾向非常明显,权力经济到了末期,经济的活力被窒息,资本只有寻求权力的庇护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人力资本亦如此)。一线城市的 明显上涨以及北京和上海的房价最近一两年明显拉开的距离,这反映了权力的价格在上升。
分母看,中国房子估值的分母太小。成熟国家中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级差地租)大部分都会被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走(不动产税、遗产税),然后再惠及全民。中国是对资本最友好型国家,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收益都归房主,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给方间接受益最大。关于这个问题华生老师写过很多文章。
所谓长效机制应该是逐步改变估值的分子和分母背后的机制。
五、关于宏观政策
要相信决策者有政治和经济整体的一套韬略。打左灯向右转恐怕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至少阶段性是这样。邓老曾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是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现在的领导也深刻承袭了这一精髓,政治的稳定将为未来的经济破局护航。目前的状态可能是时机尚不成熟,18个月内不排除主动打破僵局的措施出来。
未来经济的破局方向:约束诸侯,释放红利给民间。
为什么要约束诸侯(政治逻辑)?过去十年分权的权力被中间层窃为己有,形成负向越来越大的利益集团,所以约束诸侯是前提。约束诸侯才有可能使私人获得更多红利。
如何约束诸侯?政治上就是吏治,经济上就是财政集权(不光是财权更多是事权将再次向中央集中)。
但约束诸侯必然带来增长的困扰。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分权制下的标尺竞争(许成纲称之为“分权式威权制”),中国要改变分权式竞争体制,重构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个引擎是什么?模糊的,不清楚。
但是我们清楚,分权式竞争体制下,只要是一旦经济下滑,重启地方进行融资和进行竞争性发展的这种特征就顽强地存在。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约束诸侯程度=容忍的增长下行底线。
去杠杆的策略:避免无序相互践踏
中国手中不多的几张牌:要利用好仍处于健康状态的中央政府的表。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至中央政府的表上,统一进行债务重组。先转移杠杆,再行去杠杆,如果组织有序的话,能最大限度避免无序相互践踏,将有效缓解流动性紧张,可以降低存量债务系统循环的成本,也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裕的流动性。
所以中央政府的财政要保持适度的弹性,至少最近两年。目前公布的赤字率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财政,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财政,09年开始中国财政的实际赤字率恐怕每年都在7%以上。这个赤字水平要控制住,但结构可以变化,节制地方债务,为中央财政腾挪发债空间。
证券化和债转股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将负债久期尽可能拉长。
未来中国宏观政策考虑的方向:并不是要关死流动性的闸门,而是让流动性改道,流向效率的部分。终止僵尸信用的后果是经济短期下行的力度加大,资产价格的下跌。
如果僵尸信用真进入「破」的状态,政策空间反而豁然开朗。
强化资本项管制,可考虑“类托宾税”政策,防止短期资本大进大出;
可以迅速松绑汇率管制,增强弹性,使中国完整工业链重新获得动力,提振经常帐盈余;
甚至可以某种程度的量宽(主动推低利率水平),从而降低整个债务体系滚动的成本;
金融救助措施,进行资产置换,类似于当年AMC的撇坏账模式,如发长期低利率特别债券对现有银行债权进行购买,积极推进债务重组;
今天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来自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债务失控。整个信用系统都在套体制的“利”。而由此形成的大量僵尸型企业和资产难以灭亡,并占据和无谓消耗着大量信用资源而得以存活,导致经济生产率显著衰退。由于新增信用在越来越高的比例上被用于支持既有债务体系的循环,所以货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差,流动性内生紧张的压力越来越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