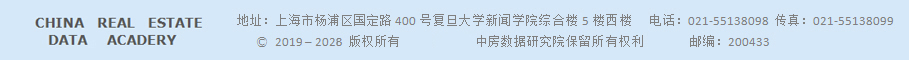第一,合理区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发挥好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一方面,运用长期政策促进结构转型,提振消费、发展服务业、制造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稳定当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短期维稳任务很重,当前主要经济政策以长期措施为主,但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风险。目前,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中国需要进一步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稳定短期经济。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风吹草动”即可引起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必须采取稳健、有效的短期措施,应对资产价格波动、汇率贬值、跨境资金流动等现实问题。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捷径”。首先,促进服务业开放,引致服务业FDI进入。结构性改革无法在短期内提振经济,但服务业FDI直接拉动投资,对提振中国经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积极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外部投资者。
当前,中国债券市场,特别是3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是国际市场少有的低风险、相对高收益资产,资本项目开放势必吸引大规模海外资金流入,应效仿1998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用国内增长潜力吸引外部投资,提高国内建设效率。最后,有效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目前,美国主导TPP协定的标志性大于实质性作用,其强调的投资准入、服务贸易、劳工和环境、国有企业和监管一致性条款代表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崭新方向。中国应积极通过BIT谈判等途径有效对接TPP,以开放促进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同时,美国也不会甘心将庞大的中国市场排除在TPP协定以外。
第三,通过市场化运营基础设施建设,盘活现金流。中国经济城镇化步伐加快和老龄化社会临近都不断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新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从地方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做实现金流促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首先,通过市场化投融资途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通过吸引民营资本促进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未来现金流应当同当期沉淀成本剥离,通过公开招标将未来现金流作为私人经营标的,提升运营效率。最后,适当出售包括未来现金流良好的优质资产在内的国有资产,减轻当期债务负担。
第四,缓慢挤出房地产泡沫,提高居民住房质量。作为重要抵押品的房产和土地仍然是目前中国整个投融资体系运作的重要工具,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会造成宏观资产萎缩、杠杆率上升和经济失速。房地产市场应在预期管理基础上逐步控制房地产泡沫,而不是房地产价格短期内的迅速下跌。在房地产泡沫得到控制前提下,中国经济需要推进未来房地产在旧城改造、中心城区空间的二次开发以及住房质量标准提高之后更新投资。13亿人口的国家和处于城市化进展中的国家,房地产业的未来还是大有发展前景的,不可能只在短短十几年内完成中国居民住房需求的使命。
第五,破除国有企业垄断,加速制造业升级。中国制造业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位置,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生产。重化工领域的国有企业垄断造成产能过剩,挤压产业链中下游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抑制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的强化将通过生产要素资源向竞争性领域的配置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企业利润导向下的投资决策将加快工业部门投资结构调整,进而促使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第六,调整央行资产负债,以外汇储备置换地方政府债券。通过汇率市场化、放松外汇管制等途径,鼓励居民和企业持有外汇、多样化对外投资,适度降低外汇储备,提升中国海外资产的质量和收益。同时,效仿美、英、日等国,以财政出资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设立外汇平准基金稳定汇率,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此同时,央行利用外汇储备减持的人民币资金购买地方债务存量,扩展基础货币投放途径、提供市场流动性,并以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收益实现央行地方债券资产的长期增值。
第七,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过市场化改革转变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保持稳健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 1998—2007 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验之一。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宏观系统性风险加剧。目前PPI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2015年10月同比下降5.9%,企业部门面对的实际利率高企。由于实体经济无法承担高利率成本,大量资金愈发在股市等金融体系空转,挤出实体经济投资。